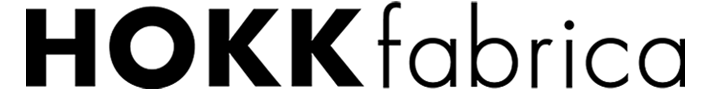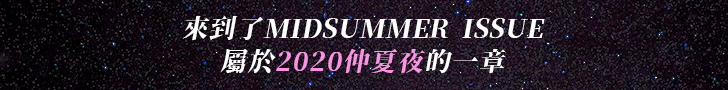Her Story專欄,我們遇見了她──跟我們一樣,又有點不一樣的她。她不一定是每個人口中的誰,但她的故事一定值得我們聆聽。
浪跡天涯乍聽瀟灑非常,可是如果要你半年不歸家,而且在海上生活,你又願意嗎?這位台灣女生,在天涯與海角間闖蕩工作,可她不是旅遊博客,也不是去了工作假期,而是因為她是一位遊輪翻譯員。讓我們來聽聽她的故事吧。

膽小的海上翻譯員
作為一位郵輪翻譯員,想必她是醉心語言或是憧憬海洋的浪孩子吧?然而,1991出生的Anna坦言:「因為其他領域我讀不來,所以就選擇成績還好的英文。」對於海洋,「其實沒有任何熱情,我們畢竟是遊輪,開船的只有航海人員,對海有熱情也只有他們,其他人都只是為了工作而已。說實在,我初初完全沒意識到我在船上,就像坐飛機一樣,我甚至連船上有駕駛艙都不知道。」
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在海洋飄泊,關於家人會否擔心,Anna戲言這是一個賣小孩的概念:「其實我很多時候都很膽小,但一開始傻傻的不知道要怕。家裡一開始是不太願意的,後來家裡有一些經濟狀況,媽媽聽到薪水時就讓我去了。」


在海上分秒必爭
從事遊輪的翻譯工作,具體來說「就是給乘客的節目資訊,像報紙、入境資訊、菜單、一些標語。或者緊急的時候翻譯船長的話再廣播。」問到最有挑戰性的部分,她立即回答:「現場翻譯!有時候太緊急,五分鐘之內要翻完一整張紙的內容,就要廣播了。」似乎在海上工作,不是想像中般悠揚,而是分秒必爭呢。
作為公司唯一一位中文遊輪翻譯員,「船上的工作沒翻完也不能走,我沒弄好大家就完蛋了,所以忙的時候可以工作到半夜12點。」聽起來好像是件苦差,可是Anna卻相當享受,「一開始的確很忙,但適應以後會很喜歡,也可以到處去玩」。
不要以為翻譯員的工作很乏味,「去年我們由台灣去沖繩縣,碰上許多颱風,大約一個星期就有三個颱風。所以我們一直在改行程,也一直去駕駛台跟船長翻譯、待命。因此跟駕駛台人員的感情特別要好,平常他們都不太跟別人說話,再者駕駛台也不能隨便進去,那個月對我來說是很特殊的經驗。」到了這時,Anna漸漸對海生產了興趣,但她笑言駕駛台人員的工作太辛苦,還是繼續當翻譯好了。


船上就像一個封閉的王國
在船上,Anna最大的衝擊是他們的階級意識,「我是很相信人人平等的那種人,但船上從吃飯的餐廳、睡覺的房間、能去的地方、薪水,全部看你肩上的條子決定,像權貴和平民」。而有條子的權貴對沒條子的平民大呼小叫,讓有話直說的Anna十分生氣。
「因為階級牽涉到利益,人們會對條子有所崇拜和渴望,得不到的人就會用一些手段親近那些肩上有條子的人。在船上就像一個封閉的王國,條子多的人會把船當成自己的王國」幸好,Anna的職位本來就有一條條子,不至被權貴打壓,然而她卻反被沒條子的人欺負。
文化就是這樣,你只能躲,沒辦法處理。
—Anna
經常被打壓的平民看見比較弱的Anna,就將怒氣發洩在她上。「譬如說我們可以去乘客餐廳免費拿咖啡,這不是福利,咖啡師有權拒絕我,一般只有在太多乘客的時候才會拒絕。但沒有條子的咖啡師就是不給我,給我臉色,說我條子不夠多。我當時覺得很委屈,後來朋友才跟我說,他們一輩子都不可能有條子,我看起來這麼年輕就有條子,他們心裡當然不滿。」


在海洋撿回自己
後來,因為Anna那「把人,當人看」的性格,這群弱勢員工,「也看出來我跟其他有條子的人比較不一樣,就對我比較好,沒有敵意」。她坦言這一切文化衝擊,不但讓她「很努力養成的『對世界的信任』有所動搖,到現在更有點摸不透自己,一方面希望自己對這個世界信任多一點,另一方面還在害怕,還沒掌握到分寸」。
所謂出走,其實不在於距離,在於踏出我們的安全區。在這趟旅程的最後,就算面對種種衝擊,就算被世界衝散了自己,也能夠慢慢地逐一撿回自己。不是破鏡重圓,而是像七巧板般,拼出新的形態,新的自己。
Photo courtesy of Anna Lee
DESIGN: CY
28 June 2017,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