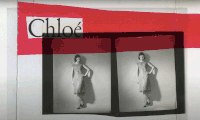怎樣才能成為天橋秀的座上客呢?誰有資格坐前排?誰不能跟誰坐?我也很好奇這些問題的答案。負責人為分配位置感到傷腦筋之餘,過程中也挖出了許多業界秘密,如據聞某些品牌曾付錢買「A-list觀眾」(大都是一線明星),又或是有人被品牌列入黑名單。不過,近來大眾對前排觀眾(FROW,front row的縮寫)都有著同一疑問:為何橋上走向多元之際,橋下卻依然是「清一色」?
「我坐在前排」是一種榮耀
「你坐在哪裡?」別少看這條問題,名義上問的是你坐第幾排,實際上則是衡量你在時尚界的地位。一般的座位編排是由品牌的公關人員所策劃,能夠坐上首排的,基本上都是A-list名人,如美國版Vogue主編 Anna Wintour和英國版Vogue的前總編Alexandra Shulman等等。當然,前排還會包含品牌的代言人和名人紅星。
到了第二排,通常會是報紙雜誌的時尚編輯或副編輯,又或是名人們的合作夥伴等;再後一排就是知名造型師或美妝師等。第四排以後的觀眾被稱為「時尚西伯利亞」(Fashion Siberia),指對品牌沒有太大利益關係、不過是一群「志在參與」的人。看到自己的價值後,有人會為自己坐第二排而感到失望,有人會因坐不了首排而拒絕參加,甚至有人會說謊,假裝掉了票,再說自己是FROW(前排)的一份子。
有關FROW的小秘密
既然前排都是時尚界的A-list,當然要好好分配位置,免得發生什麼不愉快事件。資深公關人員James LaForce曾透露,早期時尚雜誌Vogue、Elle和Harper’s Bazaar的編輯之間,必須隔開至少兩個位置;三大雜誌作為競爭關係,這個規則只想為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
那有沒有人從FROW裡被剔除?我突然想起前時尚評論家Cathy Horyn與名牌Celine創意總監Hedi Slimane的恩怨。出名說話尖銳的Cathy Horyn,當時一直對於品牌Yves Saint Laurent工作的Hedi Slimane有點微言,更說他「洗去品牌的女性優雅力量」。結果,Slimane怒氣沖沖地在社交網站發表公開信:「Horyn小姐就像是校園裡的惡霸,也有點像棟篤笑演員。」(’Miss Horyn is a schoolyard bully and also a little bit of a standup comedian.’)事件發生後,Horyn立即被Saint Laurent列入黑名單。
Video via YouTube/ Vogue
前排觀眾漸漸演變成了一種試鏡工作。由公關公司所推出的「名人採購」服務,旨在為品牌天橋秀邀請具影響力的名人參與、坐鎮。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歌手Rihanna當年參加Karl Lagerfeld 2012年秋冬時裝秀時,一共賺了10萬美元;歌星Beyoncé也曾獲得如此豐厚的酬勞。此外,品牌如Calvin Klein和Michael Kors也被指曾享用過此服務。為了確保有名人坐鎮,動輒就得花幾十萬美金,這種做法又值不值得呢?
今日的FROW又如何?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品牌花上幾十萬「邀請費」,並為對方支付航班、酒店及衣著等費用?雖然不敢說完全沒有,但這種情況已大大減少。不少品牌在籌備時裝週時,經費總是超出預算,這也變相令他們放棄投資在A-list名人之上;他們寧願把重點放在編輯與買家之上,也不想胡亂請個明星來充撐場面。
隨著社交網站的興起,一班網紅與博客成為了天橋的座上客。不用太多額外支出,便能邀請到坐擁幾百K追隨者的她們到場;只要這些紅人拍個照片,再上載至社交網站,一樣做到宣傳效果。當然,Instagram界也有A-list的代表人馬,像是最多人追蹤的歌星Selena Gomez為代言品牌Coach上載了時裝週照片,單是like的數目已高達1600萬;還有像名媛Kim Kardashian或是模特Hadid姐妹,也有相當強勁的宣傳效用。
FROW裡的多樣性問題
近日,網上時尚論壇The Fashion Spot發布了各大SS19天橋的多樣性報告(diversity report)。據主編Jennifer Davidson所言,今年是有史以來種族最多樣化的時裝週,特別在紐約時裝週,幾乎所有膚色、尺寸、年齡和跨性別/非二元代表也有出現。在慶祝橋上的多樣性時,橋下的觀眾又反映了什麼現象呢?
最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發表了文章,集中研究天橋的前排觀眾。大家知道,坐第一排的大多是業內「執政者」;比起天橋上的多種族與膚色模特,這班「清一色」的觀眾,明顯象徵了時尚界的單一。
André Leon Talley,曾任美國版Vogue的創意總監,在94年被傳媒稱為前排的少數黑人觀眾。直到現在,能在業內擔任要職的黑人確是寥寥可數:擔任雜誌《浮華世界》(Vanity Fair)時尚總監的Samira Nasr,過去二十年裡曾在時尚雜誌Vogue、InStyle和Elle工作過,她也坦言,自己是辦公室裡極少數的黑人;Edward Enninful,在時尚雜誌i-D擔任了20年的時尚總監,去年正式擔任英國版Vogue的總編,成為了史上首位黑人同志總編。如此歷史性的一刻,Enninful感到榮幸之餘,也坦言時尚界是時候作出幕後變革。
新上場的時尚雜誌Teen Vogue主編Lindsay Peoples Wagner,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無處不在與哪裡都不是〉(‘Everywhere and Nowhere’)的文章,探討黑人在時尚界工作的真實感受。在文章調查的100多名黑人裡,還包括了助理到高層、造型師到名人,以及模特等,分享了黑人在業內的實況,坦言他們永遠是佔少數。可是,很多我們「認識的名字」拒絕參加,原因是怕說錯話,怕影響自己的前途。
天橋上的變化,也許是多元的起點,但真正想扭轉這個單一現象,始終得從內部入手。筆者期待著「某某成為首位黑人/亞洲/女性總監」不再是甚麼新奇的新聞頭條,期待著將來的天橋秀,前排觀眾可以有多點新鮮變化。
Rethinking Fashion,猜你喜歡:
H&M斯德哥爾摩全新概念店,能否為低迷的銷售額力挽狂瀾?
不是所謂的時尚KOL,Robin Givhan卻在時裝界舉足輕重
風水輪流轉?被唾棄的Logo時尚,今天卻有一班忠粉
28 October 2018,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rethinking fash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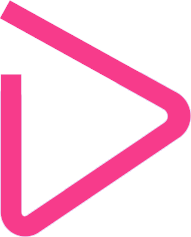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