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逢《霸王別姬》於台灣上映25週年,電影數碼修復版將在當地放映。這部陳凱歌執導、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原著小說的電影,是史上首部榮獲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Palme d’Or)的中國文藝片,至今獲獎無數。
陳凱歌口中關於「迷戀與背叛」的故事中,圍繞的是兩位演京劇的微小人物程蝶衣與段小樓,在1924年北洋政府統治的大時代下,接近半個世紀的愛恨交纏。而張國榮戲中戲所演的虞姬,歷來眾人對角色的複寫,更是令這女性形象經過各種變化。
虞姬的前麈今生
李碧華複寫的虞姬,其雛型最早可追溯至《史記 • 項羽本紀》,此角其時只為突出項羽霸王形象,提及篇幅不多。到後來眾版本,像《千金記》中沈採改寫的為顯忠貞而自殺的烈女;到京劇中梅蘭芳飾演的,為情義拔劍自刎的痴情女子;再到張愛玲掙脫男性敘事規範的版本,其女性形象隨著年代不斷改變。到李碧華手中,「虞姬」一角更化身成性別混淆的男性,陳凱歌電影改篇下虞姬亦不只一個,敘事風格更顯複雜。
雖然原著中李碧華無意側重歷史脈絡,不過電影版中張國榮演的程蝶衣這個虞姬角色,悲劇意識在複雜的歷史架構下更顯濃重;而且入戲極深的張國榮亦令角色添層電影色彩,他與程蝶衣一角於性別經驗上不論氣質或命運的重疊,抑或與角色相互相賦予的氣質個性,亦令這個「女性形象」註腳更廣。
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戲中的程蝶衣在妓院長大﹐從小給當妓女的母親艷紅當成女兒給拉扯大,這為他的性別矛盾埋了伏筆。她母親後來因無力撫養,把還是小豆子(別名)的蝶衣送進戲班,也是他性別認同改變的轉捩點。
在戲班中慢慢長大,身段纖柔的小豆子被相中演花旦,被要求唱《思凡》中的一句「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他卻唱錯成「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因而被毒打;再後來再度唱錯,給師兄拿來煙槍塞進喉嚨並往嘴裡瘋狂攪動,而這一糊弄對他的性別認同起了劇烈性影響。
這一場實質隱喻了性愛,甚至是強姦的意思。煙槍象徵男性陽具,強行的塞入比擬的是強姦過程,鮮血從象徵女性私處的嘴巴流出,這刻的小豆子猶如入戲著魔似的,打從心底認同自己是「女嬌娥」。本來強烈拒絕當花旦的他,性取向被徹底轉換。如同弗洛伊德曾說的,孩童性心理的階段最初由「口唇期」開始,就是這階段的嬰兒通過口滿足性慾,像透過吮吸等動作達而得到滿足。因此,當蝶衣(小豆子)被煙槍塞入口裡時,這一幕就起了象徵意義。而作出此舉、充當性行為施行者角色的,也就後來被蝶衣認作一生所愛、演「霸王」的師兄段小樓。
到後來程蝶衣又在張公公府邸中被強暴,後而收養嬰兒,也象徵了他對女性身份的完全認同。
不瘋魔 不成活
「不瘋魔不成活」是京劇界的一句行話,戲中程蝶衣對京劇對痴迷程度也是如此。然而,在遭遇的性別暴力中,也間接令蝶衣對戲中虞姬女性身份擁抱至深陷泥濘,分不清現實虛構。這種極致的態度,也反映在他對師傅說的,對京劇「從一而終」的教誨的踐行── 戲子的最高準則的據。因此當師兄段小樓想抽離角色不對戲,去妓女找樂子而說道,「這不大半輩子都唱過來了嗎?」時,便換來說程蝶衣的叱責:
「不行,說好的是一輩子!
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
戲中的程蝶衣就是虞姬,在此與梅蘭芳演的虞姬一樣,角色給染上男性陰柔氣質。然而戲中的程蝶衣更甚,因為他已沒法從演色抽離,昇華成「不瘋魔 不成活」境界。也因此,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捱過與師兄信任扭曲殆盡,再相逢演《霸王別姬》時,蝶衣並沒有像書原著一樣,在句「戲完了」中醒來,而是真的成為了虞姬,拔劍自刎死在霸王前。
假霸王與真虞姬
當虞姬這個女性形象,在眾來詮釋中慢慢起了變化時,霸王這強悍的男性角色也有極大顛覆。戲中戲裡霸王仍是極具威嚴,但現實中的段小樓卻是軟弱的,為活下去而將妻子菊仙和蝶衣出賣,活成「假霸王」。背叛且自私的他,與形象潑辣勇敢且剛烈上吊自殺的菊仙、篤定的碟衣形成強烈對比,霸王的陽剛形象崩塌。
女性書寫的繼續反抗
然而,電影中菊仙的自殺卻和張愛玲版本不同。菊仙的自殺行為,並不像張的版本,明顯流露出女性自主的性別意識,因此根本上而言並未逃脫出對霸王的依附;而蝶衣忠於京劇中的角色設定,也仍然處於被動的女性形象。
為此,李碧華雖然在小說版本上修改,卻堅持原作中蝶衣從戲中醒覺的結局,以堅持其逃出男權敘事的女性書寫特色。然而,到電影改篇版中,不論文本甚或張國榮賦與蝶衣一角的,令其傳奇的悲劇色彩從舞台延伸至現實。因而於戲迷而言以性別意識去討論,也未必是電影目的。
雖然戲中的菊仙於現實中的「虞姬」,與沉迷梨園夢中蝶衣演的「虞姬」,難以掙脫的父權架構下。但回到歷史語境,在無多選擇與各有堅持下,菊仙的剛烈與蝶衣極致的執拗,對比懦弱的段小樓,多少還是展現一種女性力量。
為你推薦:
5 December 2018,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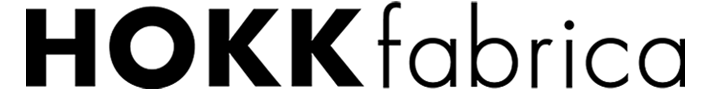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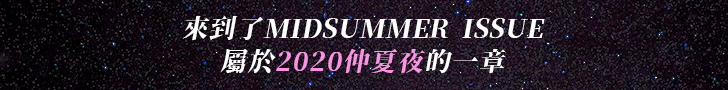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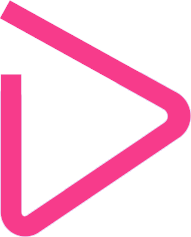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