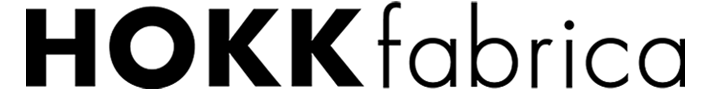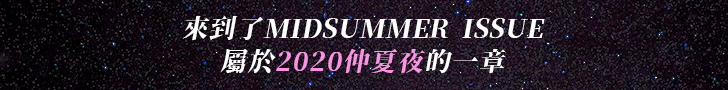HF Long Read | 在速食的年代,慢慢讀。
HF Long Read | 在速食的年代,慢慢讀。
如今筆者最熟練的動作,便是在遇到新奇好玩的事時下意識地拿出手機咔嚓一聲給自己拍張照片。Selfie(自拍)一詞誕生於2002年,到今,在Instagram上搜索「selfie」關鍵詞已經可以搜索到367,155,087的圖片,數量驚人。無論喜歡與否,我們都被夾雜著進入了一個「自拍時代」。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社會如現在一般充斥著如此高濃度的影像和視覺訊息。而文學評論家W·J·T·米謝爾(W. J. T. Mitchell)在繼「語言學轉向」理論後提出了「圖像轉向」的概念,認為如今視覺影像已經與語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圖像已不再僅僅是真實世界的再現,在其背後是真假之間更為複雜的訊息生產與傳遞過程。
或許自拍對處於日常普通生活的我們來說僅僅只是用以定格片刻回憶的方法;又或是與他人分享瞬間與故事的途徑。但在社會背景下,其作為當今圖像生產方式的一個重要版塊,或許折射出了一些現實的文化意義和內涵。
自拍一定是自戀嗎?
自拍的歷史可是源遠流長。從古時文人畫家們喜愛畫自畫像開始,自拍的雛形便已顯現。 Robert Cornelius在1839年用相機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張自拍照,當時因為攝影器材的昂貴,不是人人都能擁有記錄容貌的能力。時間走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經濟相機的普及讓普通百姓均可以拿著相機對著鏡子或自己咔嚓一聲成為自拍達人。直至2003年底,Sony Ericsson Z1010的推出第一次引入了用於自拍的前置攝像頭,至此,人類宣佈全面踏入自拍時代。2012年,自拍成為全民娛樂的方式風靡全球,甚至在2013年作為對社會生態產生重要影響的新時代用語被收錄入《牛津字典》。


自拍總是與自我迷戀劃上等號。悠久的歷史更確切地說明了自拍的文化並不是在科技時代橫空出世,其背後所體現的自我表達訴求來源於人類渴望認識自我的天性。從洞穴壁畫到手機屏幕,我們習慣於用圖像表達形象和講述故事,用符號來識別和表明身份。視覺藝術家Alicia Eler在她的新書The Selfie Generation: How Our Self-Images Are Changing Our Notions of Privacy, Sex, Consent, and Culture中表明,自我影像的記錄不應該簡單地被歸咎於自戀情節,而帶有更深刻的文化內涵。特別是自拍可以作為邊緣群體向世界展示自己存在和獲得身份認知的途徑。當無數帶有同一身份符號的個體圖像鑲刻在網絡時,它們的力量甚至可以挑戰傳統的主流權力敘事。
社會交往的新形勢──「人際交往」變為「圖像交際」
然而另一層面,在信息時代的影響下,自拍似乎從「認識與表達自我」走向了「藉助他人構建自己」;「一起拍張自拍看看」好像逐漸變成了「快拍張自拍發Instagram」。
對很多自拍愛好者來說,拍照只是第一步,只有發佈到社交平台上獲得點讚數才是自拍儀式最終完成的句號。在這個「三分靠拍照,七分靠修圖」的時代,自拍著重的似乎已經不再是呈現真實的自我,而是塑造一個理想中「美好的自己」。這個過程中,個體完成數字編碼成為了符號,變成了不斷流通的圖像化表達。然而「她真人根本就不是長這樣。」經常被用以戲謔修圖過於明顯的自拍發佈者。
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著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提出:「社會交往就像一個戲劇舞台,每個人都在扮演某個角色,在社會互動中都竭力維持一種與當前社會情境相吻合的形象以確保他人會對自己做出愉快的評價 」。我們用修圖手法和配文打造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品牌」,「圖像交際」逐漸取代了線下的人際交往活動。點讚成為了友誼的象征和心情愉悅指數的關鍵值,因此我們一直把眼睛和時間傾瀉於發光的電子銀幕上,即使是家庭聚餐或朋友碰面,比起久而未見的相互問候我們還是比較關心剛才發的照片有多少個人Like了。個人形象和生活體驗被切割成一張張碎片式的圖像,經由修圖軟件進行調味加工,再被放上社交媒介的烤爐上,精心烹製,閱後即焚。
世界上最貴的自拍──自拍時代的反思
2011年,隨著拍賣錘輕輕敲落三下,Untitled #96 以389.05萬美元的價格被拍下,這張來自Cindy Sherman的自拍作品直到現在仍是世界上第二昂貴的攝影作品。

與我們印象中通過拍攝「他者」成名的攝影師或藝術家相區別,Cindy Sherman最特別之處在於她的作品多數是定格自身形象的自拍。然而她卻並不覺得這些照片的主題是她自己,她在照片中扮演電影、雜誌、街邊或任何她想象中場景裏的角色或明星。她甚至會刪除那些與自己過於相似的照片,只是因為希望自拍的照片看起來與自己毫無關係。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這種特別的創作起源於少女時期的愛好。Cindy Sherman對各種不同的衣服愛不釋手,她喜歡裝扮自己,不是為了變美而是為了讓自己與眾不同。有時候她甚至會喬裝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去參加聚會,以此緩解自己輕微的社交焦慮。喜歡自拍的她卻完全不想要成為他人的焦點。
22歲時,她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 Untitled Film Still系列,她開始透過自己的鏡頭、用自己的身體塑造各種不同的女性形象。自拍的創作形式或許正是她照片特有風格的形成原因,在「自我凝視」下由「自身」所構建的「她人形象」,「本我」和「擬像」被同時定格共處,她挑戰著自我形象由主流社會和他人眼光所構建的社會規則。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她的照片沒有帶著修圖時代的「完美」和「精緻」,反而所有形象都展露自己無助、憂鬱、呆滯、害怕或是失落的表情。或許透過扮演這些經常出現在當時社會媒介索克華的女性刻板形象,Cindy Sherman希望讓這種違反當時審美觀的作品反過來帶來一種抗爭的力量。

Via Wikiart

Via Wikiart
這些自拍是拍給誰看的呢?她在自拍時是否能看見自己呈現出的形象?為什麼要採用自拍的方式進行創作?這些問題到現在似乎都還沒有確切的回答 。但面對爭論不休的猜測和非議,Cindy Sherman認為自己無需要解釋,「我的作品本就應該意味不明,這是它們多數取名為無題的原因」。
Arvida Byström──社交媒體時代的自拍宣言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年輕藝術家們,熱衷於探索新媒體的邊界,甚至直接將其轉換成創作的內容或工具。瑞典籍女藝術家Arvida Byström因在Instagram上傳自己以粉色色調為主的自拍而出名。她的自拍顏色鮮艷,有著這個時代特有的數碼色彩。自信地展露著少女的身體,Arvida Byström想通過自拍說明的絕不僅僅是「被觀看的價值」 。
在接受Wonderland的採訪時,Arvida Byström回憶到自己是在少女時期愛上了自拍。青少年都喜歡透過記錄肖像,從而發現世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真相。後來受到Tumblr「分享圖片」的概念啟發,她發現原來圖像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產生更大的意義。
她不再通過自拍尋找作為社會裡「客體」的真相,而是轉向通過自拍發表「主體性」的自我宣言。她拍攝和上傳遊走於社交媒體「身體規範」邊緣的自拍,質疑和挑戰暗藏在此之下大眾媒體對於女性身體的定義準則:什麼樣的圖片會被定義為裸露或「不雅照」?女性身體的照片為何總是受到監管?沒有體毛的身體才符合「女性氣質」嗎? 自拍為什麼一定被冠以「膚淺」和「自戀」的形容?
用自拍探索女性形象和性別標識,這寫或許也在提醒我們沒有人比自己更應該關注自身的身體。「美麗」從來就沒有標準的定義,然而文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經常會受到社會主流審美的影響,再反向刺激大眾文化形成「刻板」和「單一」的審美標準。其實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根本不用想那麼多。只是在按下快門前,我們可以先決定想呈現的是別人認為的美好,還是是自己最原初的表達。
同場加映:Hf Long Read
淺談《良友》畫報所刻劃的摩登女性
中國20年代興起的「天乳運動」
21 November 2018,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Hf Long Read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