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年代,我們該問一問:「究竟Gen Z是甚麼?」
相信你和我對“Gen Z”這個字並不陌生。這群人無處不在──雜誌封面、報章頭條、社交平台、廣告活動;時尚編輯和品牌都愛從他們當中找出新面孔──無他,青春總是美好,這群人身上洋溢著一份單純、浪漫、幹勁和新鮮感。他們集體被冠以「Z世代」之名,乾脆方便,聽上去充滿Cyber感;「Z世代」就是引領人們走到未來的一群人。可是,當人們談“Gen Z”的時候,他們所討論的究竟是甚麼?這個稱號背後所指向的特質真的足以形容一整代人嗎?
Gen Z vs. 00後
根據牛津字典,「Z世代」泛指那些在2020年即將成年的人,他們生於九十年代中期至2000年後,抓著「Y世代」的尾巴來到這個世界,自小便與科技為伴。今年18歲的彭愷琳Tiffany指出Gen Z有地域文化之分:「從西方角度而言,我屬於Gen Z,因為社交平台Tumblr上每個標示了#GenZ的帖文都說中了我的心聲;從香港角度而言,我就不是Gen Z,因為香港人普遍使用『80、90、00後』來標籤。雖然我屬於『00後』,但我覺得自己無論在生活娛樂還是政治取態方面都比較貼近『90後』,而且我是會用Facebook的。」當我們談Gen Z時,我們談及的不只是出生年份,更是群體的某些共性。

Gen Z 眼中的 Gen Z
究竟被界定為「Z世代」的她們,又是怎樣理解自己和朋輩呢?這是我們收集得來的答案:
有想法、有創意、有創造力、有魅力的、追求突破、不容小覷、敢作敢為、無畏強權;斜杠青年、追夢者、Social Media Addicts、The Gayest Generation、The Meme Generation、Change-makers、Rule-breakers;物質泛濫、多怨氣、自我、抑鬱、依賴性重(對科技和人際關係);跟millennials不同;並非如長輩想像中般幼稚;滿足感容易受社交媒體影響、善於用社交媒體分享個人意見和發起行動;傾向向壞的方面思考、較少去欣賞身邊事物、較少去傳遞、分享愛;思想較開放和前衛,超越了前人所設下的道德界限;兩極化、優秀的人懂得好好利用資訊媒體,但更多人卻被「娛樂至死」;經歷過911襲擊、感受到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在memes找出口在hashtag找歸屬感
彭愷琳言簡意賅地形容她那代人:「我們這一代對社交平台上了癮,有人充滿魅力、有人陷於抑鬱;我們喜歡Memes、喜歡諷刺,被虛無主義所包圍。」在人人皆是content creator的年代,一頓飯、一粒青春痘、一次失言,動輒都能成為嘲諷或發表「偉論」的材料;當中固然創意滿分,某程度上卻也反映了青年人對現實的無力,只能從揶揄和無聊的創作中苦中作樂,從memes找出口,也從hashtag找歸屬感。
現代人陷入了一種「娛樂至死」的危機
9GAG、連登、Facebook上的二次創作從不間斷地在網絡公海中漂流,流進了我們的意識。20歲、熱愛攝影的大學三年級生雷安喬從另一角度出發,看得更清晰。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她認為不只Gen Z,其實現代人已經陷入了一種「娛樂至死」危機:「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雙刃劍。現在媒體資訊發達,人們生活愈來愈富裕,娛樂生活較易滿足,大家都會追求節奏快的生活和感官刺激,這樣的環境導致部分人缺乏深度思考。我在這代看到的是,隨著科技和娛樂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知識與才智的差距變得愈來愈大。」

拒絕讓大數據去收窄眼界
「娛樂至死」這個概念出於美國作家Neil Postman的1985年暢銷著作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文書名翻譯為《娛樂至死》,書中探討現代社會資訊傳播的轉型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並由此所導致的各種問題。雷安喬擔心,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無處不在的麻醉式快樂會削弱人們對世界的敏感度,因此做創作的她會擴闊吸收知識的渠道:「朋友笑說我過著退休老人的生活──早起早睡,注重養生,喜歡看書看報,以書信溝通……我很少上社交媒體或追蹤某些平台,因為我不想被大數據算法去收窄我的眼界,不想被媒體控制思想。我討厭這種被資本餵食的感覺;我要自己選擇看些甚麼,而不是被動地讓別人給我看些甚麼。」
接通全世界 同時感覺「斷線」
21歲的香港唱作音樂人章尾而感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彷彿比以前脆弱:「一個人不玩Instagram、Facebook,又不跟你聯繫的話,這個人對這個世代而言形同『消失』。」章尾而不是一個經常上網的人,她可以24小時都不碰電話,寧願花時間行山、陪伴家人和寵物、投入音樂創作等。「『你最近好嗎?』已經成為了公式化的問候。一些帖文、文字和照片讓你以為對方就是一個『喜歡去日本旅行、喜歡剪短頭髮』的人,但這個人現實中是否真的這樣子呢?」我們了解陌生人的私生活,卻無法了解身邊的人(甚至螢幕中的自己)的真實感受;按下拇指讚好的那一刻,你心中又有沒有隱隱的浮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距離感?對於章尾而來說,一個人更加需要做的,就是不斷往內探索,了解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正如她在作品《化夢》中所講的訊息一樣。「音樂讓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誰,而『自我』是自你出生、有意識以來便需要一直去尋找的東西。」是的,就算感覺跟別人「斷了線」,也別跟自己的心靈「斷線」。

虛擬與真實之間 其實存有選擇
在香港土生土長、現於紐約讀傳播設計(Communication design)的Tiffany Tong有類似的想法:「我們這一代的滿足感多多少少都會受社交媒體所影響──科技太深入我們的生活了,深入到不能自拔,彷彿逐漸成為現代人唯一的溝通方式。」有志成為設計師和創意指導的她平時會以Instagram發佈作品,歡迎任何有建設性的意見,又會跟來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充分體會到互聯網對於新晉設計師發展的好處。她無法否認,「人與人之間確實失去了聯繫,落入一種稱之為“second reality”的超現實世界之中。」不過,她認為虛擬與真實未必一定無法共存。「你可以選擇如何呈現和表達自己,但同時我覺得人們不應該失去自己真實的模樣。」

網絡世界的真真假假,重要嗎?
2001年出生的Jasmine Chan生於Nokia揭蓋手機與iPhone的交界,她抱有另一種看法:「線上和線下的我總會有點不同。有時網上的東西不用太真吧!你上社交平台的目的是想放鬆,重點是不要過份依賴。」從不吝嗇分享生活照的她同樣感受到虛擬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落差,她也曾經因留言和批評而受到精神困擾;後來她明白到,在真假難分的網上世界,「認真便輸了」:「愈活躍於社交平台,就愈不該那麼認真看待批評和留言。」

任何稱號都不足以凌駕於自己的名字
社會愛稱呼這群人做Gen Z,覺得她們「幼稚」、「被寵壞了」、「因科技而變得懶惰」、「吃不到苦」;或許有些標籤的確可以用以形容一部份人,不過新世代的人們並不個個都同意這種看法。14歲的Shannon Sin 玩了七年的劍擊,嬌小的個子撐著十多公斤的裝備,不時參與本地和外國的比賽;遇見Hf之前,她連「Z世代」這個字都沒有聽過:「今天的世界傾向評論多於認識,人們都還未花時間了解一個人,主觀感受老早已經給那個人的為人下定論。單憑一個字又怎能夠形容一整代人?」考完DSE、剛推出首張個人專輯的18歲歌手黃淑蔓也有同感,「唯有你自己才能定義自己是誰。我們的思想並不真的那麼受資訊科技所影響,我們受過教育,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說到底,Gen Z都是另一種以偏概全、另一種社會定型。其實,任何時代都總會出現一批青年,因為他們所相信的價值和信念、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同,而跟社會產生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叫社會不知道如何接納他們或跟他們相處,於是便產生了不同的偏見、定型甚至否定。19歲的是一位詩人、藝術家兼禪修者,她認為:「硬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放在這些分類之下實在太過守舊、死板了──我們有著無限可能,不斷改變,不停流動,有著各種面向;將自己變成一代停滯不變的人可說是一種罪孽。我們不應該限制自己。我們這一代超越了任何人所給的標籤、任何人所給的評價。」

的確,正如Tiffany Tong向Hf提及,「任何稱號都不足以凌駕於自己的名字本身,『女權主義者』、『亞洲人』、『Z世代』統統都無法取代『你』自己。」
點擊下列連結,了解Words of Women專題更多!

25 July 2019,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Gen XYZGen ZHer StoryHong KongWords of W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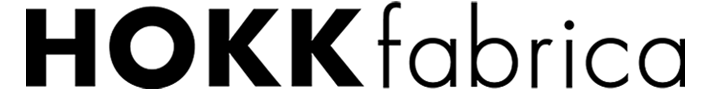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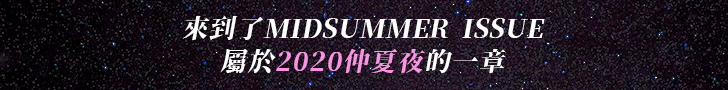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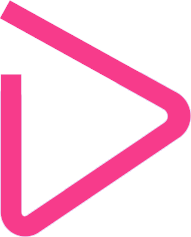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