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文化中,「孤獨」這回事總是差勁的,孤獨的人總給認為奇怪、出格,行事特立獨行而不跟禮俗,以至推論出這類人是危險的;這種污名主要來自人對群體文化過份擁戴。關於個體與群體間的取捨與平衡,或者可以以台灣美學家蔣勳在《孤獨六講》中的見解為主軸,來個淺談。
孤獨者
說到孤獨者,蔣勳在書中提起了法國小說家卡繆的《異鄉人》(L’Étranger) ,一個改編自真人故事;內容講述,作為主角的年青人莫名其妙在太陽底下,開槍射殺了一位阿爾及利亞人。為此他解釋道:「我殺人,因夏日陽光刺眼。」雖然原因荒謬,但更荒謬的事發生在審判過程,所有舉證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他最終被當成謀殺犯的原因,是他在母親喪禮上沒有掉眼淚、喪禮後與女友到海邊度假及發生性行為,或在喪禮上未打上得體的領帶。換句話說,青年人的錯來自對他不順從世俗標準如守孝道、缺乏群體意識。


‘L’Étranger’一字中譯解作孤獨者,書中男主角與群體的脫節本來無關道德判斷,然而犯錯後,這種孤獨特質卻成為他「變壞」原因。由此可見大眾對人性的孤獨,已不期然加入了一種善惡觀。
孤獨就是怪異/奇怪?
孤獨的人,在社會上被視為怪異、甚至會構成危險。記得早前無意中聽到一位單身舊同事說:「我也想找好對象,但總感覺單身的人是奇怪的。」乍聽怪怪的,因為這其實是單身者對同類的一種偏見,與「沒有朋友的人是奇怪」的說法同出一轍。不論你缺乏的是朋友還是伴侶,反正在群體文化主導下,個體最好還是隱沒在群體中,才不至變成異類。
蔣勳特指,主流之所以排斥個體生活,其實是受儒家文化影響:儒家所強調的文化禮教無法以個體達成,而是靠五倫去維繫;任由時代如何變遷,社會要維穩,仍逃不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些關係網絡,於是「孤獨者」就可憐地繼續成為狙擊對象。
關於荒涼──那是寂寞還是孤獨?
但群體中也未必沒有「孤獨」這回事。現代人交流的媒介,總逃不開冰冷的電子產品。在這些虛擬空間中,所有物事稍縱即逝,如蔣勳書中所言,「說話的人很多,回話的人很少」。書中很有意思的一句──「城市比沙漠還要荒涼,每個人都靠得那麼近,但卻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與孤獨處在一種完全對立的位置,那是寂寞。」這是蔣勳對寂寞和孤獨的看法:前者令人發慌,後者卻令人飽滿。如果叫人荒涼的是寂寞,那麼在拒絕孤獨前,不如先區分清楚所經歷的,究竟是寂寞還是孤獨。

對蔣勳而言,孤獨讓一個人懂得悲憫、能看到世界更多的面向;這種與世界保持的距離,也維持了個體的獨立,以跳出大眾的既定思維。不過孤獨僅是陶醉於個人世界嗎?其實於他而言,這也是連結群體的方法:當人透過孤獨對自己認識得更深時,才能以更完整的自己與群體互動,以不至像「盲頭烏蠅」般,在群體中失衡。
來源:《孤獨六講》(2007)。 蔣勳 著,聯合文學出版
為你推薦:
Through Our Lens:所有孤獨與寂寞,他們都用腳尖承受
DESIGN: SONIA/ HOKK FABRICA
1 October 2018,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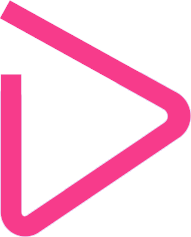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