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F Long Read|在速食的年代,慢慢讀。
「舞著,華爾滋的旋律繞著他們的腿,他們的腳站在華爾滋旋律上飄飄地,飄飄地。 」
–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時間的消逝,新舊的交替,令許多東西漸漸步向歷史。舞廳,一個散發著上世紀色彩的詞語,同樣也成為一段留不住的復古回憶。在那光怪陸離的舞池中央,大家伴隨節拍擺動著身驅,甚至有人會拿著酒杯向著鎖定的舞女進發。談起昔日的夜生活,特別是為人熟悉的上海百樂門舞廳,那聲色俱備的空間之中,曾經發生過無數不為人知的夜半故事。



舞廳的兩面性:正當娛樂與罪惡根源
在上海開埠初期,跳舞沒有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可能是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仍未完全散去,這種摟抱之舞一度被視為有傷風化,因此成了西人的「私家玩意」。而隨著西方的交際舞、爵士樂及現代舞的慢慢傳入,加上西化思想的不斷滲透,跳舞終於變成一道時髦的熱潮。在20年代初期,許多上海人也被這種新興娛樂所吸引,不少舞廳更在短時間內累積了不少熟客。但畢竟許多人也非跳舞能手,故當時出現了不少專業舞蹈教師及舞女,令這道舞蹈熱得以發揚光大。到了30年代,隨著消費文化及物質水平的大大提升,舞廳也迎來它的黃金時期。以上海為例,單是舞廳就已經接近40間,其數量比起電影院及劇院還要多,可見跳舞正式變得通俗化。
雖則跳舞文化逐漸受到萬千寵愛,惟大家對於這種新型娛樂卻持不同的意見。作為忙碌的都市人,特別是那班終日兀坐於辦公室裡的他們,每天也期待著週末的來臨。因為只有在假日裡,大家才能相約三五好友出外消遣,並在舞池裡愉悅奔放地跳著交際舞或探戈,又或是優雅地跳起狐步及華爾茲來。當然,這種想法是把跳舞視為正當健康的娛樂活動。正如著名散文家兼學者梁實秋的「舞廳之旅」,令他坦言做了一夜噩夢:
「東是一塊肉,西也是一塊肉,這裡是一根擦粉的胳臂,那裡是一條擦粉的大腿!
還有一張一張的血漬似的嘴,一股一股醉醺死人的奇香奇臭……」
– 梁實秋《老憨看跳舞》
這個肉慾縱橫的時刻, 似乎也暗示了一班舞客與舞女的曖昧關係。在許多平民式的舞廳裡,如當年卡薩諾拉或戴蒙特舞廳,這種「肢體關係」可算是隨處可見。尤其在昏暗的封閉空間裡,某些舞客醉生夢死般跳著舞,並趁機摟抱不同的女子,以尋求一種肢體接觸的快感,簡單來說即是「吃豆腐」。甚至有人把舞廳變成色情場所般,以金錢來換取與舞女們的性關係交易。由此可見,當時的舞廳被看成是上海罪惡的淵藪之一,並認為這與銷金窟沒有分別。


上海百樂門舞廳,已成過去「東方巴黎」
縱使舞廳引起無數爭議,但談到十里洋場裡數一數二的代表,那就非百樂門(The Paramount)莫屬。即使我們不是生於老上海,但筆者相信很多人也耳聞過「百樂門」,而且它也在近年被再度翻新。這所擁有「東方巴黎」美譽的舞廳,曾代表著一種摩登的生活品位,更在30年代掀起了一道獨有的舞場文化 。
1933年12月14日,剛好是令人期待的「TGIF」,百樂門舞廳舉辦了一場盛大無比的開業慶典。在當時的上海市長吳鐵成夫人以金鑰匙打開那道花崗石大門後,數千位賓客正沿著那華麗的大理石台階,並慢慢步入不同樓層的舞池及宴會廳。被邀請前來的人,大部分也是上海的名門望族。至於初期的門票售價,平日是每張四元,週末則是五元,而到了節慶日的價格會更高。以30年代的薪酬分佈作計算,車夫的每月薪金大約有10元,而上海的小學教師月薪為30元,編輯可能也是40到100元不等。因此,能夠到百樂門的人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至於百樂門的幕後推手,不能不說上海本土建築師楊錫鏐。 作為當中的投資者兼設計師,他不但偏愛著裝飾藝術(Art Deco) ,更想把百樂門營造成一座中西合璧的高檔舞廳。故從取名、選址、設計到觀演空間,百樂門的出現既標誌著現代上海舞場文化,同時亦被人不斷地模仿。
百樂門,英文取名為Paramount,其解作至高無上,更有「通往百般快樂的門」或「一進此門能得到千百種樂趣」之意。在選址方面,它並沒有坐落於某個地理位置方便的「旺區」,反而選擇了連接著外灘與高檔住宅區的中間地帶。刻意遠離繁囂市區及住宅區,實際是想為人們提供一所能夠逃離日常的世外桃園。而百樂門的門面設計,也沿用了楊錫鏐最愛的裝飾藝術元素—充滿現代感的流線型立面,滿佈了橙色和棕色釉面板,還有垂直線條窗和幾何線條的點綴等等。還有「百樂門」的招牌霓虹燈,不但成為了上海夜生活的標誌符號,更曾被《申報》描述為「電燈喚車機關」,讓車夫們能夠輕易地找到要車的舞客。
樓高三層的百樂門,建築面積超過2500平方米。二樓的主舞場裡可容納400對賓客,三樓則可容納200多人,故有了「千人舞池」的美名。與一般的舞廳相比,兼具繽紛及裝飾藝術風的百樂門為客人提供了一種好萊塢式的想像。在開放式的舞池裡,客人既可輕易地成為表演者,在「舞台」上成為自導自演的明星,又可以隨時成為觀眾,在舞池周邊閒談飲酒。更重要的是,百樂門是一所提供「純娛樂」的高檔舞廳,即是客人們都會自帶女伴,裡面沒有聘請任何職業舞女。如此與眾不同的定位,難怪令百樂門成為了老上海數一數二的繁華舞廳。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舞女的悲慘宿命
獨樹一幟的百樂門,成為了舞廳界的「例外」。但談起上海舞廳文化,舞女的確是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特別是都市人的享樂精神,也間接推動了大量的消費品出現。不同於香煙與酒等物品,舞女成為了一種視覺性的消費。她們佔據了舞廳的主舞台,以迷人的舞姿去誘惑男人;台下的觀眾一方面充當配角,另一方面則在宣洩生活裡的壓抑與寂寞。大量的舞廳出現,無疑是為舞女開僻了表演舞台,但這班搖曳身姿的女子,或者有著很多身不由己的故事。
在二三十年代,作為消費女郎的舞女曾受到不少詬罵:「舞孃們的心尤狠,慾望尤奢,嘴上是蜜,臉上是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衣著裸露,打扮過於時髦,輕易與舞客發生性關係,猶如妓女一樣,專門騙男人錢財與感情,這些狠話基本上是把舞女營造成「最毒婦人心」的形象。然而,不少人卻對這班出生卑微的弱女子心存同情。就像是台灣作家白先勇所寫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以「一晚」的視覺濃縮了金兆麗的舞女生涯:
「四十歲的女人不能等,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功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
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麽,四十歲的女人到底要什麽呢?」
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女主角金兆麗所身處的台灣「夜巴黎」,其實是對百樂門的一種回憶移植。作為舞女,年青的她在百樂門曾風光過,甚至以為自己找到真愛。可惜「舞女」的身份,注定她要活在一個污濁醜惡的環境之中。除了每晚被色迷迷的眼神所「強姦」外,同時又被愛人的家庭嫌棄。隨著年紀漸老,金兆麗深知自己沒有本錢,也無力作出掙扎,因此只能想方法把自己嫁出去。為了討得年老富商陳發榮的歡心,她不惜拉面皮,扯眉毛,勒肚子,以這樣自虐式的手段去保存自己的花樣年華。
或者有人會覺得,舞女只是想要釣個金龜,過著奢靡生活就是人生勝利者。惟曾經相信真愛的金兆麗,被利欲熏心及人情冷薄的舞廳世界所扼殺,甚至令她放棄對幸福的追求,成為一個潑辣女人。這種性格的扭曲,不但成為了自己的保護罩,或者也意味著舞女的悲慘宿命。


參考資料:
梁實秋:《梁實秋文集(第二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
吳健熙,田一平编:《上海生活(1937-194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
14 December 2021,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Hf Long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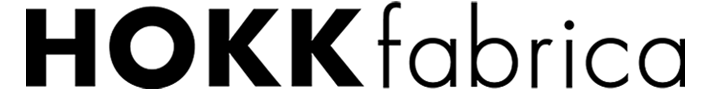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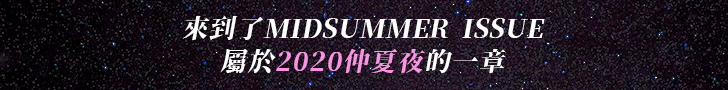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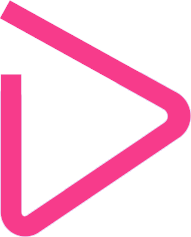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