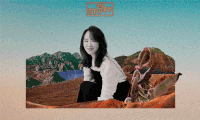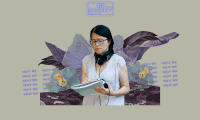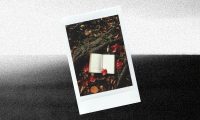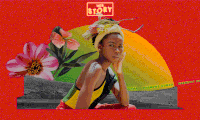如果地球另一端有一個跟自己相同樣貌的人,會不禁飄渺的想,她聲線怎樣?心思、氣味、喜好和思想又會不會和自己相近?又或者「我們」會否像《兩生花》那樣,時刻都感受到對方存在的氣息?
當世界容得下兩個樣貌相同的人,又會否容許她倆走向對方跟前,抹去難以解釋的迷霧而相知相遇?
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以《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1991)訴說生命的微妙、宿命這個命題,俯視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和錯過,以及不經意的交疊而引起的因果變化。

兩個相同樣貌的女孩同樣叫維朗妮卡,同是感性又敏感,波蘭的Weronika是女高音,法國的Veronique是小學音樂教師。兩人有許多相同的小習慣,會用戴戒指的手輕撫臉龐,同樣是個喜歡音樂的小妮子。一個在台上高唱荷蘭作曲家Van den Budenmayer的作品,另一個則教學生彈奏此曲。兩人互不相識卻經常感應到對方若即若離、若隱若現的氣息,感覺神秘又吸引,親切但疏離,這不是神經質,也不是疑神疑鬼,無線索無目的一直尋找彷彿不存在的另一個我。
Veronique把夢到對方房間的掛畫擺設告訴爸爸,疑惑地問自己是否有個孖生妹妹或姊姊,爸爸的回應當然沒有肥皂劇般那樣戲劇性。直到有天Weronika在台上演唱高音時心臟病突發身亡,Veronique頓然若有所失,感到莫名失落而悲傷痛哭。

頌讚希望美好的天籟歌聲驟然斷了音,以為這個世界冷漠又殘忍,但生命裏所有不着痕跡的瑣碎,都是生命與生命的交流和對話,只是不被知曉也不被察看。當Veronique翻看照片上與自己相同樣貌的女子,兩人早已在波蘭華沙廣場上擦身而過,亦無意間把對方的身影攝下,Veronique才明白自己為何會一直心緒不寧,突然無端傷感,兩顆敏感的心靈早在生命的一角緊扣不放。

Weronika和Veronique在尋找失落的另一個「我」來完整自己。Weronika在這一邊廂,享受浸沉在音樂之中用歌音頌唱人生美好,最後死在高台;那一邊廂的Veronique檢查得知有心臟病,於是忍痛地放棄唱歌事業而轉行當音樂教師,在小學遇上木偶師Alexandre,尋得真摰的愛情。
Veronique仿似為Weronika繼續未完的生命,甚至透過Weronika遺下的生命牽引來填補自己所缺乏的。正如Alexandre對Veronique解釋製作兩個相同木偶的原因,是因為木偶很脆弱。生命的無常,宛如這對兩生花,一死一生,人事世物總有微妙的更替和變異,也是萬物的恆常。

能夠相遇,或不曾相遇,乍看無關痛癢,但冥冥中有着不經意的安排。世界似乎為每段生命歷程埋藏了微妙的線索痕跡。如果可以追認所有生命的脈絡,可能有無數的絲線連接到天上人間,生命線的一動一靜、一收一放都牽動着生命中的種種可能。能夠相遇,或不曾相遇,都隱含不着痕跡的因果關係。緣起,而不滅。
人雖渺小脆弱,但當生命的微小細碎不經意地敲起樂音,你會驚嘆、感謝這份之於生命的美麗和感動。亦幸好世界上有奇斯洛夫斯基,讓我們能夠透過他的電影和鏡頭欣賞關於生命種種的微妙可能、感知世界的神秘和變幻。
All photo via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film stills
9 March 2017,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