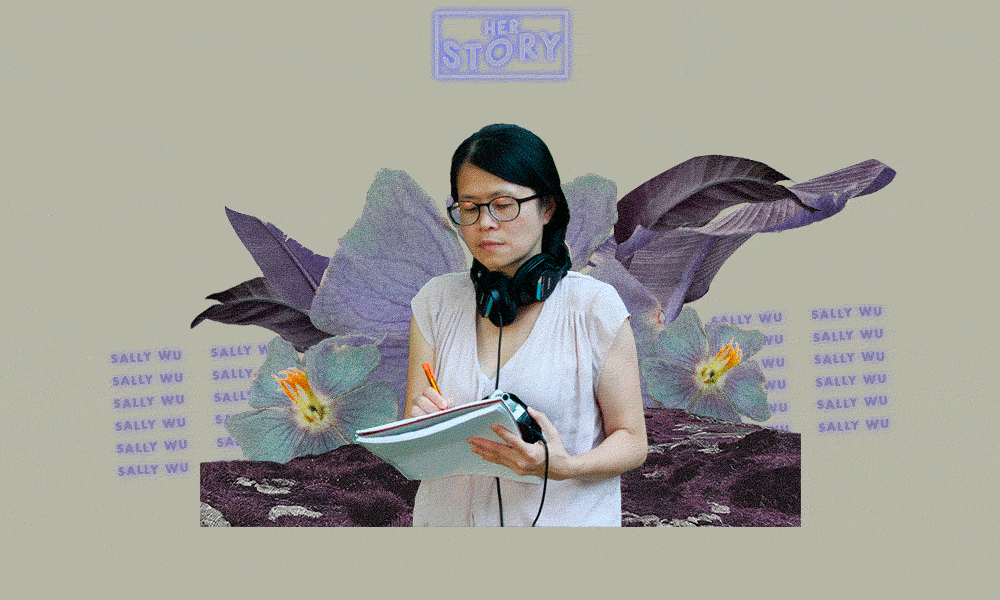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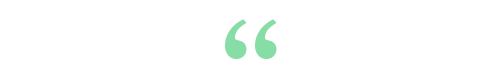
每個人都會想往前走,但走的腳步是輕是重,那是另一回事。即使有袍袱在,還是往前走,才能看到更多的東西,以及遇見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 吳郁瑩,紀錄片《阿紫》導演

在過去一年,我們熟悉的日常變天,眾人都在忙於反應、忙於適應、忙於生存,相信大多人都巴不得這年快點過去,重新出發。然而,在急著拼棄,跑得老遠之前,在躊躇放下與執著之間,驀然回首,發覺原來可以帶著過去前行。臺灣導演吳郁瑩的紀錄片作品《阿紫》中,每一個人物的人生都好像沒有選擇的餘地,想要展開自己未來,又總是脫開不了命運與責任的牽絆。

每 個 人 都 會 想 往 前 走 , 但 走 的 腳 步 是 輕 是 重 , 那 是 另 一 回 事
來自越南的阿紫為了改善家中經濟狀況,選擇嫁去台灣;生於台灣的阿龍,因小時候的一次高燒而不良於行,本來沒有打算成家,可是在母親的要求下迎娶了阿紫這位外籍新娘。不敢逆母親之意的阿龍,同時又會瞞著母親給妻子寄錢回鄉。某幕,阿龍淡然地感嘆,阿紫替父母蓋房子後還要幫哥哥蓋房子,好像永遠不能放下原生家庭,去把生活的重心放回照顧自己在台灣的家。我們也許不是外籍新娘,不過這種移民的矛盾似乎不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而原來導演吳郁瑩本身也是一位「新住民」,定居美國東岸:「我跟阿紫一樣去了另一個國家,有了家庭以後就好像要生根了,可是父母仍在台灣。我不能陪他們是我的袍袱之一。阿紫決定嫁去台灣的時候,沒有去想到底生根是什麼樣的感覺,有了小孩才去思想跟這個地方的關係,以及跟自己國家的關係。我相信每一個移民都一樣經歷著一種異地感、孤離感,那種疏離感沒有太大的差別,更何況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嫁過去,她的整個心境的感受會強很多 。」


「其實我覺得不是阿紫不想,她也知道小孩子是她的重心,一個人要背負著兩個東西去往前走。其實她才三十幾歲。我覺得媽媽是女人最複雜的一個角色,讓女人蛻變到另一個階段。她也意識到要為了新生命負責任這件事,她一定會move on,但是她會像腳上拉著很重的石頭去往前走。每個人都會想往前走,但走的腳步是輕是重,那是另一回事。即使有袍袱在,還是往前走,才能看到更多的東西,以及遇見生命更多的可能性。」她思量半晌,續說:「我就是放不下對台灣的情感,所以才會回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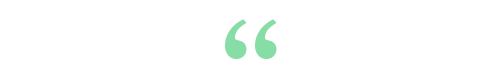
我想要的東西會很努力去得到,很清楚我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
– 吳郁瑩,紀錄片《阿紫》導演

再 多 的 文 章 與 報 道 , 都 不 及 這 一 顆 顆 牆 上 的 蒼 蠅
《阿紫》整部片子以畫面主導,「所有的場口用Fly-on-the-wall*的方式拍攝,不去打擾人物之下,把當時發生的真實捕捉下來」。導演吳郁瑩用真實的情景、真實的人,溫柔地去刻劃女性、家庭等議題,因為她相信:「聽到跟看到的畢竟還是不一樣,那些東西不見得是語言能夠表達出來的。」(編按:Fly-on-the-wall是一種拍攝紀錄片手法,攝錄機有如在牆上的蒼蠅只是記錄房間內的情況)



說起那些不能言喻的情感,吳導演不能不提在越南的拍攝旅程:「我去之前知道他們的歷史,但真正去到那樣又是不一樣的感受。其實他們都是生活非常辛苦的人,但他們再怎麼貧窮,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力。他們跳舞的氣氛,其實蠻強烈的,他們喝酒跳舞,把自己的情感釋放。那個東西是你讀再多的文章、再多的研究、再多的別人寫的報道,都沒有辧法感受出來。」

「這部紀錄片當然很大部分是讓台灣人去了解新住民,不一定所有的人就像主角阿紫,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複雜性。其實不只台灣、不只亞洲,西方國家也有非常多的外籍新娘。許多人對東南亞女孩子一般的認知就是窮,可是每一個女孩子都有她們最獨特的感受,每個人背後都有故事。」導演吳郁瑩對自己作品最大的宏願,就是觀眾願意去多了解他人,願意深入的去看每個人;放諸宏觀,政策決策者也應該用這個方式去看她們,而不是很單一地看待。

![]()
with
吳郁瑩
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就是⋯⋯
當媽媽。
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的一件事⋯⋯
以前希望成為很厲害的小說家。
我生命中最大的「為什麼」是⋯⋯
為什麼不同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環境會把最簡單的人類塑造出不同價值觀、道德底線,這股力量到底可以有多大?
我想讓正在閱讀的你知道,⋯⋯是沒有問題的
青春的時候所有的感覺,無論是危險的、超乎道德底線的,都是這個年紀你有的權利,自由去感受那些東西吧,一切都沒有問題。
愛不總是⋯⋯
愛不總是別人說什麼是愛就是愛的,這是一個很個人的,是自己純粹的感覺。
我希望我能說得更多⋯⋯
我希望我能說更多人的情感微妙之處的事情。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
我永遠不會忘記十幾歲的女兒還是會很甜蜜的叫我媽媽,把她的頭放在我的肩上的畫面。
如果我能看到未來,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人類是不是就這樣子一直循環下去,我想知道人類是否仍然沒有從過去的錯誤得到教訓。
All photos courtesy of the interviewee, HKA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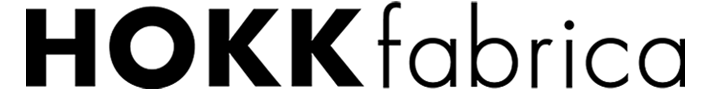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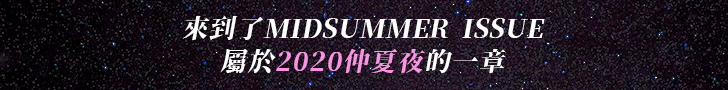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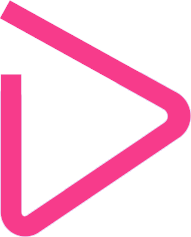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