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荷里活再度因起用異性戀演員出演同性戀角色,而受到外界批評。姬蒂·白蘭芝( Cate Blanchett )為異性戀演員辯護,亦表明立場,反對演員須經歷與角色同樣處境,才能演活角色這觀點,認為這違背了表演意義。
「我誓死捍衛『姑且相信』的權利,演出超出自身經驗的角色。」
“I will fight to the death for the right to suspend disbelief and play roles beyond my experience.”
編按:「Suspension of disbelief」是一個由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若作者能夠在虛構故事中注入人性化的元素,使假象看似是真實,那麼讀者便會姑且放下故事是否真實的懷疑,享受故事的發展。
兩種聲音
這已不是單一事件,上兩個月施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亦因同類批評,因此放棄扮演變性角色。坊間主要反對聲音是認為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Transgender)這類角色,應交給真實LGBT演員飾演才合適。而這裡實質上,大概夾雜了兩種考量,一是如姬蒂·白蘭芝反對的,認為由與角色有相同經驗的LGBT演員,才能真正演活角色;另一把隱藏聲音,是認為這些為數不多的LGBT角色,應給真實的性小眾演員,以保障他們的權益。或者會疑問,為何不是能者居之,而一定要把角色分配給圈內性小眾,這便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為何最佳男演員獎,從未頒給出櫃演員?
英國國寶級演員伊恩·麥基倫爵士(Sir Ian McKellen)早些年已經提出這個問題,為何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從未頒給出櫃承認自己同性傾向的演員,但因扮演LGBT角色而獲獎的異性戀演員,卻大有人在?麥克萊恩爵士補充,這是因製片方擔心要是讓同性戀演員擔當主角,會令觀眾感不舒服;相反,若由直男演男同志,觀眾大概會覺得演員勇敢,且沒了以上憂慮。而明顯這裡要提訪的,是因恐同情緒導致觀眾流失的局面。即是說情況要是的確如此,就算有性小眾角色,真正的性小眾也沒有發揮空間。
白蘭芝:對藝術的一種藐視
這裡要是只用第一個觀點──演員須經歷與角色的同樣處境,才能演活角色的觀點,是有點站不住腳的。演員非為性小眾,卻因演活性小眾而獲認同的例子不為小數。單是白蘭芝便因電影 Carol(2015)和I’m Not There(2007),出演性別經驗與自己不同的角色,獲不少獎項;而且如白蘭芝所說,這種觀點本來也是對藝術的一種藐視,亦否定演員能力。
既得利益者
但直男或直女成功角逐或演活角色時,是否真可以理直氣壯?這樣說是因,如果電影圈真存在忽略性小眾權益這事實,直男或直女大概便是既得利益者。這種排斥性小眾演出LGBT角色的局面,並不是他們有意造就,但佔了便宜卻是事實。或者白蘭芝也會站出來說,「那就來個公平較量吧」,但若情況若真如麥基倫所說的,整個電影工業逃不開恐同情緒,這便不是簡單的異性戀和非異性戀演員之間的角力,而是一個更宏觀的考量。
「Inclusion Rider」
這令人想起了麥杜雯(Frances McDormand)早前因演出電影《廣告牌殺人事件》(2017)一角,獲奧斯卡影后獎項時的致詞。她在台上提出了引自Stacy Smith的「inclusion rider」(包容性附加條款)概念,提倡演員在簽片約時,為保障電影能如實反映現實,選角時需依劇本,須確保整體演員的族群比例、性別、政治傾向、語言,乃至年齡分佈等,能達至合理水平。條款除了旨在讓電影還原真實外,也確保性小眾和殘障演員等,能獲得公平對待。
「政治正確」的理由
這種「政治正確」說法和做法,當然激盪人心,但還是留下不少尾巴。最突兀的還是回到白蘭芝的觀點,為何需要有真實經驗的演員,才能駕馭角色?不過要是單是以保護弱勢族群為由,這種說法還是說得通。雖說荷里活總不乏宣揚公義的電影題材,但現實中,內部的性別、種族、性傾向歧視或剝削等問題,還是屢見不鮮,這種堅持以性小眾出演LGBT角色的偏袒﹐還是不無道理。
為你推薦:
打破刻板形象:我是同性戀,但是……
In The News:就在宣布清理同性戀內容後,微博馬上又逆轉這政策?
Digisexual: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以外,未來可能還有「機械戀」
DESIGN: CHRISTY/ HOKK FABRICA
22 October 2018, 12:00 P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LGBTI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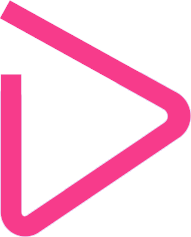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