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個年代對於精神病的定義詮釋都不同。同性戀曾被當成精神病的一種,而不願意服從丈夫指示的女性也會被送往精神病院。似乎正常與歪斜間的界線早已模糊,在Nellie Bly的《瘋人院十日談》(1887)中,精神健全的作者竟然在通過兩輪精神病專家的診斷後住進了女子精神病院十天,與其他精神病患一視同仁地看待和相處。


Could I pass a week in the insane ward at Blackwell’s Island?
I said I could and I would. And I did.
(我能夠在Blackwell’s Island上一週嗎?我説我可以也會做到;然後,我真的做到了。 )
Nellie Bly雖然沒有豐富的記者經驗,但她接到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這個十日瘋人院的報道挑戰, 二話不説便接受了;也讓她成爲出版界中響亮的女性名字,膽色過人的她,除了站在瘋人院前綫體驗和報道,亦成爲環繞世界一周的旅行報道家。
延伸閱讀: Her Story:堅持報格,捍衛新聞自由──Katharine Graham
由誰定斷的失常?
Nellie Bly從接到劇本那刻,便開始在家裏的鏡子練習失常的模樣,眼睛要瞪大一點?表情要緊綳一點?這些我們想像中的失常定型,對她來説都是管用的。

不久,她就發現,行爲、表情越正常,説話越理智,就越被視爲失常。( Yet strange to say, the more sanely I talked and acted the crazier I was thought to be by all except one physician )其實打從進入精神病院的一刻,她就停止演戲,但卻被視爲扮作若無其事的失常女子。
延伸閱讀: 看完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的心情少不免是痛苦的
中途居所作序幕
住進精神病院前,她選擇到女性的臨時住所(Temporary Home for Females, No. 84 Second Avenue.)居住,進入收容貧窮和無家可歸女性的中轉居所之後,也意味著她的計劃開展了。
Here was a home for deserving women and yet what a mockery the name was.
(這是為有需要女性而設的家,卻有著如此諷刺的名字。)
收容所裹光溜溜的地板、沒有檯布的木餐桌、質料廉價的床單,她視這些爲文明的反差。詫異於所謂用來庇護婦女的地方竟能如此簡陋,她詳細列出這裹的膳食不過是簡單的麵包、開水煮的牛肉、薯仔和咖啡,全裝在破損的盤子上。
中轉居所內有著社會容不下的貧窮女性,她們卻沒有如常人一樣被好好善待。不過當作者以爲這裏的膳食和裝修已經足夠簡陋的時候,隨著書中內容推進至後半部,我們會發現同樣是收容婦女的精神病院,情況比起這裏還要更差。
令正常人變瘋的地方
What, excepting torture, would produce insanity quicker than this treatment? Here is a class of women sent to be cured.
(除了虐待,還有什麼比起這種「治療」,更能使人快速瘋狂?這班無助的婦女,原本是送來這裡接受療癒。)
在Blackwell’s Island精神病院,Nellie Bly詳述了病人被護士粗暴對待、溫飽不足 、衣衫單薄、寒冷至極的待遇。午餐基本是一杯粉紅色的稀茶,配幾顆梅子、一塊發霉的麵包;晚餐是壞掉的肉、只有一湯匙分量的湯、發霉的麵包和冷掉的馬鈴薯。起初她完全吃不下這些膳食,但是後來飢寒交迫,不管什麽食物,她都得吞下。
洗澡是猶如地獄一樣的體驗:在寒冬下,病患排隊用同一缸冷水、同一條毛巾,護士粗暴地洗刷她們的身體,然後渾身濕透地套上單薄的睡裙,披著濕漉漉的頭髮躺上硬如木板的床,床上的毛毯更短得不能同時遮蓋肩膊和雙腳。可是護士們身上卻穿著足夠的禦寒衣物,懶理三番四次苦苦要求一件披肩的病患 。


病院內的日子基本上不能稱作生活,早上六點到傍晚,病患被迫坐在一張長椅上,不許動彈,不許説話,敢站起來的病患只會遭到護士暴力對待。偶爾會有散步時段,但那只不過是在優美的大自然環境中,排著隊、綁著走路的環節而已
… give her no reading and let her know nothing of the world or its doings,
give her bad food and harsh treatment, and see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make her insane.
Two months would make her a mental and physical wreck.
(不讓她閱讀,好讓她與世隔絕;不給溫飽,嚴刑對待,看看將她迫瘋要多久。兩個月,足以讓她的精神和身體瓦解成碎。)
這些貧窮女性,或者是被迫送進來的精神健全者本應需要悉心照料和關心,但在不見天日、飢寒交迫的精神虐待下;再正常的人,身心也會遭重創。而且大部分都會被迫瘋,因爲連最後一丁點意志都會在這種環境下消磨掉。想要逃出病院更是天方夜譚。
是精神病,還是被放棄?
19世紀中至後期,即《瘋人院十日談》面世的時候,女性精神病患,有時候只是虛構的婚姻失敗副產品。女性被要求百分百順從,一切事務都由男性決定,女性只需遵從和執行指令。雖然如此,一旦遇上家庭關係和婚姻失敗,不會以離婚收場,因爲離婚是一種污名;相反,假如女性顯示出反叛的取向,丈夫就會宣稱自己的妻子精神失常,將她送往精神病院。
But here was a woman taken without her own consent from the free world to an asylum and there given no chance to prove her sanity.
在《瘋人院十日談》中,我們還見到女性因言語不通被送到病院,德國女子Louise Schanz就是其中一個,醫生聽不懂她說的德文。孤寂一人的她,沒有任何辯護的機會,儘管精神沒有半分異常,卻因爲身份不明被送進病院,而作者見證了她由正常到被迫瘋的過程:在日復一日被看護拳打腳踢,洗澡、膳食等不人道對待中,還發起了高燒,開始出現幻覺。當作者完成十日的臥底調查, 公開發佈文章後,重回病院時,Louise Schanz已經被調往另一個院舍。
這也讓人不禁想起甘乃迪家族的Rosemary Kennedy。她有學習遲緩的問題,而且行爲反叛,也有今天所稱的抑鬱症。但是她的父親認爲她的行爲不符合家族期望,也不夠優秀,為她擅自安排進行腦白質切除手術(prefrontal lobotomy)。今天,我們知道這個手術只會以失敗和毀滅告終,而在當年,這項手術是用作治療同性戀者、性生活過於開放的女性和罪犯。進行手術的有八成是女性,但裏面又有多少人是自願接受手術的呢?Rosemary Kennedy也並非自願,最後她失去走路和説話的能力,被送往紐約的精神科醫院,消失在公衆的視綫之中。診斷精神病患,成了一種隔離異類的手段,基本上,在《瘋人院十日談》的案例和甘乃迪事件中也能看到:進入瘋人院的人,并非真的瘋了。
十日談後,是一個霸權的終結
Nellie Bly魚目混珠地混進精神病院再出版書本一事,讓精神科醫療體制公開受到挑戰。這次臥底行動迫使日後的診斷制度變得更爲嚴格,衹有被判斷爲 極爲失常的人才被送進病院;這也防止了社會迫害和隔離女性,而過往被嚴格診斷,判斷爲需要入院的抑鬱症患者等,現在都會改以藥物治療,而非幽禁和剝奪其自由。 同時,精神病院的資金大大增加,讓這些收容病患的地方再無藉口剝削病人應得的糧食和衣服。


Nellie Bly待過十天的Blackwell’s Island精神病院,則在書本出版七年之後關閉。她在寫完《瘋人院十日談》之後,挑戰環繞地球一周,記下旅行見聞以《環遊世界80天》一名出版,她的名字也成爲女性記者列表中,不可不提的一個傳奇。

References:Library.upenn.edu , AsylumProjects , Kqed.org , Medium & Social.rollins.edu
推薦給你:以女性角度,執起電影作者的「筆」──導演
DESIGN: BIRD M/ HOKK FABRICA
13 May 2018,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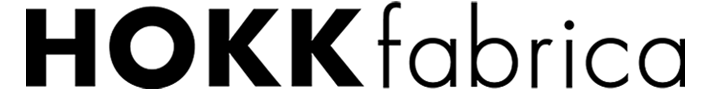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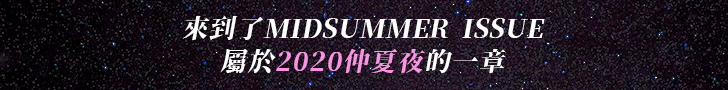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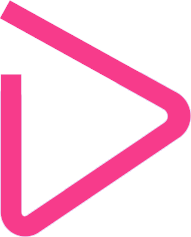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