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寫是絕對的自由」,破除最大的禁忌,遊走性別與種族疆界。新書《蓉蓉》寫亞裔女同志的情慾探索、沉溺與對抗,關於一段花開不結果的愛情,關於如何自由定義自己,理直氣壯抓住酷兒身份。這次Hf邀來了作者盧妤,與讀者分享她的創作歷程。
Hf: HOKK fabrica | 盧妤: 盧
Hf:新書《蓉蓉》最初的構思是如何而來?
盧:最初只是很單純的想要報復對方對我的無視,於是就決心寫一本書,要以「永恆」去對抗「暫時」;要以「認真」對抗「輕浮」;以「我」去對抗「你」,要想盡辦法讓蓉蓉無法無視我。
Hf: 對於「蓉蓉」這個人物,最初的創作靈感何從而來?
盧:一個失敗的戀愛對象就是最好的書寫對象。
Hf:《蓉蓉》看似是個關於沉溺的故事,你怎樣看待當中的自由或束縛?
盧:書寫時是絕對的自由,書寫過去就是從束縛中尋找自由。過去的事情已經無可改變,不過如何詮釋就是自由的彰顯。沉溺,大概是那死心眼還未開吧(笑)。

Hf:現實中的你如何看待一段沒開花結果的感情?
盧:沒開花的花該放一邊,找一棵盛開的木棉花。
Hf:蓉蓉遊走於性別與種族疆界,你如何理解這位酷兒的身體流動性?
盧:她的身體是她行使自由的唯一工具,他在男生女生一人二人之間來回游走,身體成了試煉場,提煉一個最貼近她心目中的自己的自己。唯有破除最大的禁忌,才得以把最真實的自己釋放出來。
Hf: 能跟我們分享故事中那些情慾探索,與蓉蓉角色酷兒身份認同的關係嗎?
盧:蓉蓉對自己的國族身份非常困惑,那是個看似黑白分明卻佈滿灰色地帶的空間,或非常容易受到質疑的領域,反而情慾探索讓她為所欲為,自由地定義自己,是個讓她有安全感和自主權的身份,也不用怕別人的挑戰或質疑。女同志,是她唯一理直氣壯的身份。
Hf:「甜蜜和距離」是很多戀愛關係的寫照,你自己如何理解?
盧:我曾經讀過一本書,說愛情有兩個敵人──距離和親密。這兩個東西是要不停調節,跟情人討價還價所得的。距離像砒霜,份量剛好就使你美艷動人,過量則中毒身亡,當然,當愛上一個人的時候,這些理論都可以統統拋諸腦後。
Hf: 蓉蓉角色在傳統性別論述中置身怎樣的處境?
盧:性別論述對她無關緊要,一個脫離了異性戀常規、父權和母職的女同志,理論上是最自由,最能為所欲為的一群。可是以後殖民論述來看,她大概還要很多時間才得以脫離潛移默化在她體內的殖民主義。

Hf:可以分享多些關於《蓉蓉》中的「赤裸」或「曖昧」的部分?
盧:如果沒有情慾,我寧願不寫。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只不過不想把真實隱去,加上《蓉蓉》的文體是個人絮語,所以落到情慾的部分就自然把想法沒有忌諱地寫出來。我們自言自語時,總不會審查自己的吧!
Hf:書裡不少呢喃細語,這種瑣碎敘事與酷兒經驗有關係嗎?
盧:內容愈瑣碎微細,愈跟酷兒經驗相連,那些呢喃細語的內容把身為酷兒的獨特經驗書寫出來,以表達當中的普世價值或只此一家的私密。「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句六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的標語仍然適用,個人範疇的事情亦有其政治性,以個人代表集體,讓讀者由理解個別同志以了解同志集體的掙扎。
Hf: 你十來歲時已接觸同志研究,這種視野如何影響之後的創作?
盧:接觸同志研究後就是我的啟蒙時期,那些理論提供了一個與別不同的角度,一套理論一個世界,自此得到思想上的自由,加上我性格比較無拘無束,有了理論後更理直氣壯。
參與同志運動時都是以文章介入的,那些性別意識已經在腦裏非常牢固,到寫作《蓉蓉》時,非要描寫一個無畏無懼,打破傳統的角色不可。為小眾充權,大概成了我寫作的使命。
Photo Courtesy of Lo Yu (盧妤)
如果想深入理解《蓉蓉》這本書,歡迎參與以下分享會與作者盧妤進行更多討論,詳情如下:
第三屆香港同讀文化節
酷兒同讀會:把悲傷留給誰?──《蓉蓉》分享會
日期: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三十一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
地點: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一樓藝廊
盧妤Facebook專頁
為你推薦
DESIGN: CHRISTY.L/ HOKK FABRICA
26 March 2019,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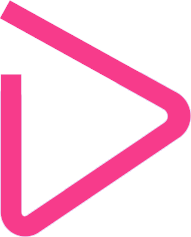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