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 0 1 9 年 秋 季
按 此 進 入 H f 的 異 色 世 界
轉 動 繽 粉 ,
色 空 互 替 ,
於 閃 爍 間 一 探 虛 無 實 在 。
轉 動 色 輪 , 輪 上 1 2 色 瞬 間 化 成 一 片 白 , 彩 虹 被 還 原 成 為 了 光 。 閃 爍 間 又 隱 約 見 到 彩 虹 的 痕 跡 , 像 幻 影 或 泡 沫 , 色 與 空 互 相 交 替 。 在 最 後 一 個 月 , 我 們 將 會 重 溫 國 王 的 新 衣 , 又 進 入 一 個 沒 有 顏 色 的 世 界 , 用 五 官 探 索 顏 色 的 虛 無 與 實 在 。
◊ ◊ ◊
在今屆艾美獎(Emmy Award)獲獎名單中,人氣劇集Killing Eve(港譯《血腥迷戀伊芙》)的女主角Jodie Comer和編劇Phoebe Waller-Bridge都榜上有名(雖然最後Phoebe因另一部自編自演的劇集Fleabag而獲獎),Killing Eve風頭可謂一時無兩。雖然表面看起來,這部劇是毫無新意的「貓捉老鼠」式犯罪題材,但細看之下就能發現劇集與傳統犯罪類型的片集有所不同,其中很明顯的一點就是Killing Eve中潛移默化的女性主義元素,就如同一杯蘇打水,無色無味,為psychopath電影帶來新面貌。

英國電影理論家Laura Mulvey曾在70年代發表過一篇著名的評論文章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她在文中指出,在傳統荷里活電影中總會有兩種角色:一種是為了滿足男性觀眾慾望的角色,另一種角色是為了讓這些觀眾有代入感、但卻比觀眾本人更理想化;隨著劇情的發展,這兩個角色漸漸相互吸引,從而完成觀眾融入電影的「意淫」。由美國演員瑪莉蓮夢露出演的電影《大江東去》(River of No Return)和黑白電影《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都屬於該類型的電影。
角色設定一:來去匆匆的女殺手,隱約如毒花惹蝶

如果用Laura Mulvey這篇文章的觀點來看Killing Eve,情況會非常有趣: 女主角之一的Villanelle是某神秘組織的殺手,然而她不是那種穿著緊身衣、超短裙、踩著「非常離地」的高跟鞋飛簷走壁、在男性審美角度而言非常性感的女人。相反,她有著自己的時尚品味,劇中不少搭配都讓觀眾讚歎;她並非超模身材,但她身上的衣服都有著獨特的氣質;她不僅容貌精緻,還非常活潑有趣;因為是精神變態,所以她對情感有著異於常人的理解方式,一言一行時常充滿黑色幽默,像一朵有毒的花朵,明知危險卻仍有男男女女對她著迷。


角色設定二:隱藏在人群中的平凡英雌

另外一個女主角Eve本來是英國情報機關的普通職員,每天朝九晚五地處理機關裡瑣碎的日常事務,過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開會遲到、與同事打賭開玩笑,和任職老師的丈夫過著平凡的生活。不過與常人不同的是,Eve有很高的智商及判斷事物的能力,每當她質疑上司的辦案能力時便會自己偷偷進行調查,並差一點就成功阻止Villanelle的殺戮;上司對她私自行動十分不滿,於是將她開除,不過她的能力卻引起軍情六處的關注,她被招攬至一個秘密行動小組,亦繼續追查Villanelle的行蹤。

擺脫男性凝視,女性間的相斥相吸
若Killing Eve是一部傳統荷里活電影,那麼Villanelle便是「代表男性觀眾慾望」的角色,而Eve則是「讓男性觀眾有代入感但更加理想化」的角色;然而,事實上Villanelle並不是根據男性審美「度身定做」的角色,她的吸引力不分性別,加上Villanelle喜歡的對象也都是女性。Eve則根本不是一位英雄式的男性,而是一個和屏幕前的女性觀眾十分相似的普通女職員,劇中她遇到的日常瑣事是你我的生活都會發生的,只是她比我們當中的大多數更要聰明機智,後來在行動小組的工作也更驚險刺激;換句話說,Eve是為女性觀眾定制、令她們代入感但更理想化的人物。Villanelle與Eve初見面便惺惺相惜,逐漸被對方吸引,如同屏幕前的觀眾對Villanelle的感情越來越深。

女性主義如無色無味的蘇打水滲透全劇
除此之外,劇中還有很多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情師:Eve的前男上司作風較優柔寡斷、甚至是膽小懦弱,與Eve後來的女上司那雷厲風行的處事方式形成鮮明對比;妻子僱兇殺掉出軌的丈夫,雖然劇情沒有明確告知,僅僅以丈夫死前對著妻子懺悔告白作為暗示。或許這是這部劇的精明之處:乍看之下是一部犯罪劇集,情節緊張連貫,沒有刻意營造出為女性主義搖旗吶喊的氛圍,就像是沒有顏色和味道的梳打水,但卻在細微之處逐漸滲透,喝下去會發現有點不一樣,讓觀眾不知不覺間接收了女性主義思想。
Killing Eve播出后受到廣泛喜愛,就連Taylor Swift都盛讚:
I’m just sort of obsessed with all things Killing Eve…I don’t think we’ve really seen such a lovable psychopath, where you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her but you should not.
我沉迷於和劇集Killing Eve有關的一切……我們從沒看到過如此可愛的精神變態(指Villanelle),她會令你想跟她在一起,即使你知道不可以這麼做。
——Taylor Swift

演員及編劇們接連獲獎,也是業界對劇集的肯定。只是經過前文將這部劇集與Laura Mulvey所說的傳統荷里活電影比較後,似乎難以想像如果將Killing Eve放到40、50年代播出會如何令人震驚,相較之下,如今觀眾們似乎對劇集並不那麼吃驚,畢竟近些年來以女性觀眾為目標或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多,例如編劇Phoebe Waller-Bridge的另一部劇集Fleabag、以「小丑女」Harley Quinn為主角的電影Birds of Prey,以及當下的熱門劇集Why Women Kill(《致命女人》)。

或許我們可以將之看做女性主義的階段性勝利,但其實我們離完全的男女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歷史並不一定總是往我們所認為的「先進」方向發展。在荷里活電影業早期,女性的地位遠比如今高,台前幕後都不乏女性身影,還有不少女演員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然而,從1916年開始,女性在荷里活地位越來越低,一方面因為早期的電影人更關注的是電影的娛樂價值而非社會價值,一些女性相關的社會問題因而未獲關注,女性電影人無法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華爾街資本介入荷里活電影工業,大型公司和連鎖影院紛紛佔據重要地位,女性便成為了弱勢,不少女性開辦的獨立公司紛紛倒閉。如今女性主義在影視作品中崛起或許並非單純的因為大公司和資本家「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女性觀眾是重要的消費群體。墨西哥美國演員Salma Hayek Pinault認為,女性不但掌控家中一切事務,如今更是養家糊口的人,成為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而這股力量則打開了缺口,讓女性電視作品掘起。這種來之不易的階段「勝利」我們要格外珍惜並確保這「勝利」是可持續的。

從蘇打水到白開水,女性主義的日常化
像Killing Eve那樣將娛樂性和女性主義融合在一起或許是不錯的方法,既避免了觀眾對「口號式」刻意宣傳的疲乏,又能讓女性主義悄悄地刻進觀眾的心中。最極致的女性主義大概就是我們都忘記了「女性主義」,讓這種思想徹底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們之所以做一件事不是為了促進女性主義的發展,而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樣做是理所當然,平淡如沒有任何添加、無色無味的白開水一樣,每一天都不可缺少。然而,我們要記得,這種透明的無色其實是光的十二色聚集在一起才能得到;如果有一天,女性主義成為「無色」的日常,那便是經過多少代女性波瀾壯闊的奮鬥才得來。
Cover image via movie still of Killing Eve

同場加映
DESIGN: CHRISTY.L / HOKK FABRICA
28 October 2019, 12:00 A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Killing Eve血腥迷戀伊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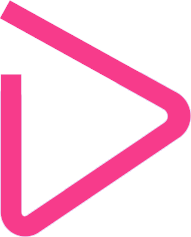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WATCH | 如果地球能聽見,你會對地球說一句什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