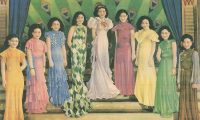《鏡子 》Mirror(1975)是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透過回憶來觀照自身,以及「記錄」回憶的電影作品。電影就如一面鏡子反芻塔氏自己的一生,包括童年的成長與母親的關係、對祖國蘇聯難以割離的情感、與前妻分離的遺憾……他在電影無盡的低怨吟哦,仿如對自己施加長期的折磨。




越是哀怨痛苦的回憶,就愈像鬼魅般纏着自己,一生不離不棄,這就像電影中,男主角夢到年輕的母親俯身洗頭那幕黑白的慢鏡:洗髮後,長髮遮臉站着,屋內的天花石屎隨水滴一拼落下……以非現實的處理主觀的想像與回想,不按時序地穿插在主角的回憶與現實之中。加上由同一個女演員來分飾年輕時的母親和主角的太太,以同一個男孩分飾童年的自己和後來自己的兒子,淡化了時間的脈絡之餘,也將父親與自己的影子重疊,象徵主角重蹈父親的過去──跟妻子離異,令兒子同樣經歷父母離異的童年。
從鏡子看進去的畫面都是將時間凝結的夢魘,過去回憶、夢境與現實時空「重疊」接上,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生命糾葛永無休止,內心的罪疚與童年時的不安註定會像鬼魅般纏着他一輩子。
或許每個人的回憶有時候都帶點「可怖」的想像,但不是那種帶驚嚇性的「可怖」,而是關於不敢直接回望的人生愧疚、或是無力可處的情感壓力。電影裏有幾幕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詭異,或許是基於每當塔氏回望自己的童年時代,失婚後的母親向朋友的妻子借錢幫助、獨力照顧自己和妹妹等等的片段等,觸痛了沉重而悲傷的深心處,使內心充滿異色恐怖的內疚與自責,故此他記憶中的色調是恆常的陰鬱冷清。


在《鏡子》中,時間不是重要的線索,抽象且碎裂的記憶情感才是盛載了塔氏個人對過去的情緒。確實,要呈現個人的意識影像,多點會抽離現實,而塔氏的電影以詩的邏輯來追溯人生,以充滿詩意的影像來訴說他對生命、以及藝術之於生活的看法。正如塔氏在《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一書說過,詩是最貼近生命的本質。詩意的影像也是展現真實生活質感的載體,既表現到思想的真實情感,亦表達到意識流動的虛幻。然而,當中與每個人生階段產生藕斷絲連的關係又是多麼的含糊不清,於生命中是不能輕易消磨。

電影中的詩語獨白,以及在畫面中烙下的留白詩意,彷彿是塔可夫斯基對不可彌補的過去作出囈語細唸的追悼。
或許能夠自由出夢入夢,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孑然身輕,而是一趟飽歷精神與心靈痛苦的過程。
All photo courtesy of 《鏡子 》Mirror movie stills unless stated otherwise
31 January 2016, 1:33 PM
HOKK fabrica
原來不只一種模樣
Contact us | 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未經授權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More: BlueForSudanFilm Cl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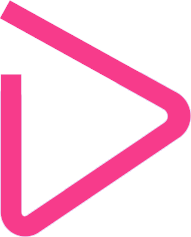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
WATCH | 若然世上再沒有「美、醜」二字...|BEAUTY SPEAKS SEASON 3